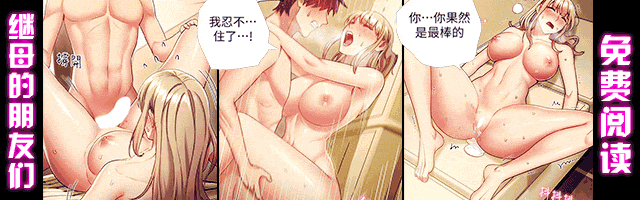手腕儿上的圆环指头粗,牢不可破,韩铭一个alpha使出全力也弄不弯它一丝弧度。韩铭感到力不从心,摸不着头绪,只好将之归结于秦柯神神秘秘的手术的术后反应,和身体里未代谢尽的麻醉的残留的副作用。
操作台上又硬又冷,被他这么一折腾,倒是温和了不少,贴上去不再像被拽上来的那一刻那么冰冷。韩铭的皮肉都黏在了上面,稍微一动就是尚未风干的肌肤表面和钢化操作台面挤压挪移发出的“啪唧啪唧”的令人不适的活动声。
韩铭老实下来,秦柯像是在暗中窥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似的,总是能卡着点出现在他面前。这次也不例外,韩铭刚安静下来不过两分钟,紧闭的房间门就打开了,穿着规整的身影复又出现在韩铭的视野里。
或许是专门设计成这样的,韩铭护着蛋,跪趴在摆放在房间正中央的坚硬操作台上,直对着大门。此刻秦柯一进来,一个笔直地站着,一个五体投地地困在台子上,看上去就像是在俯首称臣一般,韩铭还未开口,地位就生生低了一截。
秦柯步态稳健地走进来,面上闲适,有什么好事情如愿发生了似的,看到韩铭趴伏在面前,甚至起了心情逗弄,道:“倒也不必如此欢迎我,起身吧。”
韩铭气得牙痒痒,任谁先前逃跑失败又被原样儿捉回来都不会畅快,心里头畏惧懊恼和被捉弄过后的愤怒叠加,混合成一种忐忑的嚣张气焰,开口就骂道:“你个阴险狡诈的小人,你”
打定了主意要逃离这个人的努力就这么被轻而易举地破坏了,像是一个被挥散的肥皂泡,那么令人不放在眼里。韩铭现在一点也不想靠近秦柯,更不想被勾起那惑人心魄的攀至极乐的回忆,做出了尝试却迎接的是失败的结局,还可能伴随着对方的报复性举措,这沮丧几乎要淹没了他。
不必说姿势,就他这样的想法,也已经将自己放在了下位,克制不住控制不得,一喜一怒情绪和身体全部掌控在别人手上的滋味儿并不好受。
韩铭趴在被体温捂热了的台子上,身体弱点再一次被暴露在空气中,相似的姿势足以令他感到不安。
秦柯一眼风扫过去,韩铭被唬得吓了一跳,以为对方要对自己动手动脚,话也磕绊了一下:“你又想对我做什么!你都困了我这么久了还不够吗!”
秦柯绕着他转了一圈,不紧不慢地欣赏着他这副样子,道:“我思前想后,你待在别墅里一点贡献也无,不如干脆变个性别,也好符合了你现在委身于我的身份。”
“什,什么叫变个性别?”韩铭狐疑地捕捉到了关键点,牙齿悄悄地咬紧了,眼睛追着秦柯的身影,快要看不到了扭过头掰着身子姿势奇怪地试图看清秦柯的表情。
“你当个alpha实在是浪费了,不如干脆当个oga吧,反正你也只是在别墅里什么都不干地发呆,变个性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秦柯手掌一合,继续说道:“这下你不仅是珍惜的二次分化的经历者,还是这个世界上首个经历了三次分化的人。”
“这么多让人羡慕的好事,怎么就都让你赶上了呢。”
“你开玩笑的吧!”韩铭大喊出声,嗓子差点破音,“你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怎么可能呢变性哪有那么简单,是你说说就能做到的事吗?”
尽管没听说过医学上在这方面的突破,韩铭也只听说过beta和alpha相恋的人里有去接受子宫植入手术的,只为了满足alpha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这种手术的失败率很高,甚至可能对身体产生很大的伤害,一般还是很少有人会去做这种选择的。
但是秦柯的表情并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他也从来没有在韩铭面前流露过任何生活性的鲜活情绪,连刚进门的那么一句不带嘲讽的逗弄都实属难得,又怎么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这完全没有意义。
他不过是睡了一觉
韩铭的眼前出现了醒来时在自己身上看到过的那一道刀疤,发出的声音哆哆嗦嗦的:“你你不会给我植入了植入了”这太超出他的想象,他说不出口。
一个顶天立地的堂堂alpha,身体里怎么能拥有那么畸形的东西存在。他不能接受这种假设,急需从秦柯那里得到准确的答案。
韩铭的心高高提起,秦柯终于满足他,不再卖关子,唇角的笑意泄露了他此刻的心情,眉眼间皆是对自己的能力的自信傲气。
“我只不过是找出了将alpha顺利转化成oga的手法,但你转化的时间太晚了,又是从alpha过渡成oga,孕囊早就萎缩,只好通过体外移植的方法将你作为oga所缺少的一应部件儿都补齐了。”
“不可能!”韩铭大力挣扎起来,身体在钢化操作台上摔得噼里啪啦作响,“这不可能!我不信!我是alpha!我才不会是oga!你骗我你骗我!”
韩铭的身体在操作台上左扭右扭,像一只从茂密的树冠上不慎掉落
在四十度高温炙烤的地面的毛虫,即使是在挣扎,力度也和它本身的存在一般微不足道。
他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身体使出来的力度不及先前三分之一,不论是速度还是准确度和力度,都呈现出剧烈的下降趋势,与其说是在挣扎,放在施暴者的眼中不过是放不下面子回应的虚伪的欲拒还迎式讨好。暗巷里的妓子们在床上使尽手段勾人的时候偶尔也会伸伸胳膊动动腿儿,摆出一副暴雨中的娇花儿似的柔弱无助和坚持的倔犟的神情以满足身上的人的隐秘的心理需求,他的这点力度在一个alpha眼里完全是不够看的。
几分钟前他还不以为意地认定这削减的力度不过是来自于手术麻醉注入的影响,现在想来真是天真得可笑。
刀子都动了,怎么可能仅仅是为了给他刻上和许砚相同的伤痕。
“我才不要变成oga!“韩铭仍旧不放弃折腾,过度充沛的情绪将嗓音压扁,听起来有些不那么像他,“我才不要变得那么弱!这种只能被人操的家伙我怎么可能变得和他们一样!”
“放开我!秦柯!你这个疯子!”
秦柯面上的笑意消失了,一缕发丝遮挡在眼睛上,拢了一层暗影,让这个人无端显得有些阴沉。
“你就这么讨厌我送你的礼物?你试试就知道了,一会儿保准你被我操得只会哭着求我。”
“呸!”韩铭看不见后面,依然狠啐一口,“谁要你的礼物!你个胆小如鼠的家伙,敢不敢把我放开了,谁操谁还不一定呢!”
秦柯面无表情:“你好像还不知道什么叫oga……”
他将自己的腰带抽走,接着说:“希望等下你能有点自知之明……别再这么闹腾了,让我省点心不好吗。”
“非法监禁和手术,你凭什么要求我安分?”韩铭表情愤恨,手掌握成了拳头。
秦柯的手指撇开他撅起的屁股缝儿,指尖沿着尾椎骨向下移,在那个闭合的小口前停住,使了点力度逆时针转圈揉按,给韩铭一种轻柔的安抚似的错觉。
下一刻,alpha粗大的性器抵上了他毫不设防的穴口,不待他有所反应,就硬生生地破开穴口的软肉挤进那个窄小的通道。
哪里有什么温情在,不过是动手前的踩点儿,摸清了地方就以暴力突击。
韩铭被惊得大叫一声,表层破裂的痛感霎时间在脑皮层炸裂,韩铭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冷汗直冒间想到了某次应酬过后从路过的一间没关严的门缝里瞥见的淫乱景象。他看见一个筋肉发达的alpha,正按着比他身材要缩水两倍不止的oga往他下体里塞一只玻璃杯。透明的玻璃杯将男孩儿的身体撑成一个大张的扭曲的黑洞,将光线收拢在身体里面。oga的腿向一只求救无门的细瘦的手,在半空止不住地颤抖。韩铭醉酒间不由得对这番景象啧啧称奇。
下一秒男人突然暴怒,半举起了oga往地上一丢,韩铭仿佛听到了oga的身体和玻璃杯一同碎裂的声音。然而事实上这声音太过微弱,连oga的惨叫都被alpha捂在了掌心里。
“叫什么叫,别给我吵到别人了。”那个alpha说道。
韩铭摇摇自己半醒不醒的昏沉沉的脑袋,无动于衷地从半开的门口走过——他可没多余的时间烂好心,家里还有个不听话的oga等着他去应付呢。
韩铭在这一刻忽然懂得了那个男孩儿闷死在身体里的碎裂声有着如何巨大的痛苦。
或许这就是报应,他想。自己当年对oga的烦恼苦痛如过眼的云烟般无视掉,现在也轮到他碰上了一个自己毫无抵抗能力的强大alpha。
他曾经没有将oga放在心上,如今他成为了一个oga,也不会有alpha愿意把他当作一个人看。
oga。他经历的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身份——oga。痛觉神经欢乐地在脑袋里跳跃,韩铭的精神无比清醒——疼痛给人以清醒——他的心沉下去,觉得自己好像,大概,或许真的曾经对不起过自己的oga。
尽管他现在还未将一切想明白,但依照秦柯摆出来的这么多暗示,他应该是真的做错了什么。
韩铭只想到了这一点,更多的等不及他去思考。那颗坚硬的,仿若最坚不可摧的石子般的龟头依然推进到了他的身体深处,那些盘附在茎身上的青紫色的经络好似一条条自冬眠苏醒过来的小蛇,格外得活跃精神,愈发膨胀地将自己和裹住了茎身的软肉紧紧地缠绵在一起,依恋着这个小小的温暖的洞穴像是依恋着春天带来的脉脉的暖意。
至少有oga手腕儿那么粗的阴茎可劲儿地往里探往里挤,带着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执着信念只想着要把自己的整个头和身子全部都塞进去。
韩铭根本没有机会做任何准备,这次连心理上的准备都极度缺乏。毫无防范的软肉只觉被滚落的重石碾压过一遭似的,仅仅是这么一下子,就被打击得体无完肤,变得蔫哒哒的,瑟缩着,怯生生地缠附在秦柯的性器
周身,像一个温热的加湿套子,将肉茎裹上一层红艳艳的,靡丽无比的鲜亮釉膜。
疼
真的很疼。
最初的一波儿精神冲击过去,韩铭赶紧大喘一口气,憋久了的肺部隐隐发痛,像是突然被人用针刺过,他的胸膛一下下地往里收缩,呈现出一个自我保护的弧度。
在他看不见的身后,只见那浅浅的一个点被撑成了一个大张的圆形,周遭的肌肤被拉作薄薄的一片,将本就细腻柔滑的皮肤绷得似是要透了光去,仅留一点极淡的粉色,像是大病初愈后的一抹血色,在粗黑的阴茎下被衬托得愈发单薄起来,可怜可爱,却不惹人怜惜,让人只想更加凶狠地对待它,在这脆弱的地方全部打上深深的印记。
秦柯调整好了自己的姿势。钢化操作台就是专门为这个时刻设计的,韩铭整个身子都待在台面上,距离台下的人却不会离得很远,恰恰屁股的位置卡在台面和空气的分界线处,往前一步让人难以够到,往后一步又会将自己吊挂半悬在操作台下。现在这个位置不远不近,胯部一挺就可以将自己全部送进去,方便得很。
他充血的性器在韩铭紧绷的身体里搅了搅,硬挪出了几丝活动的余地,让自己在里面待得更舒适了一些。
最强烈的痛楚逐渐变化作绵长的,翻涌江水似的阵痛,只在秦柯前前后后抽动的时候发作得最厉害,偶尔对方发善心似的停顿的那两三秒给了韩铭片刻的喘息机会。
能发出声音后,韩铭忍不住仍旧叫出了声,好像声音能带走一部分疼痛似的:“疼呜慢一点好难受啊啊啊”
尽管一次都没有得到过安慰,他依旧叫着:“别别动啊好疼呜”
“疼?”秦柯当作没听到似的,甚至还觉得这声音如此美妙,比起助兴用的音乐和酒来也毫不逊色,“你不是早就习惯了这点疼了吗?”
“我没有好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