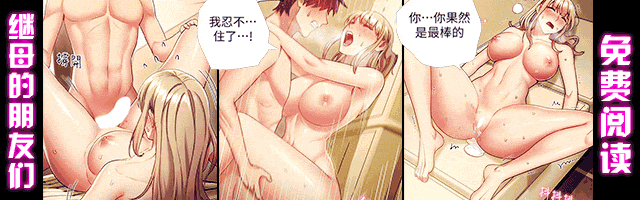温清淮瘫坐在椅子上,只能靠椅背支撑全身,身子有些发软,腿也在抖,大腿根部发麻,还能闻到空气中情欲过后的一点雄麝的香味。
舌根也有些酸麻,倒不是对方吮吸的多用力,都是他自己想轻薄对方,纠缠许久也不愿意从对方嘴里出来。
温清淮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丝凌乱,哭毁了戏妆也难掩那勾人的诱惑的一张媚态的容颜。
他端详着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突然笑了,笑着笑着就笑出了泪来。
无关悲凄,喜极而泣。
他变得不像自己了,他从前鄙薄戏文中或是私奔或是殉情、或是因为情情爱爱而迷失自我的才子佳人。
如今唱戏终成曲中人。
夜已深,最后一场大戏唱到多半,台上一出场便赢得满堂彩的戏子声音微微颤抖,从他出来的那一刻起,竞拍就已经开始了。
直到一张张纸彩被送到后台,那最别致的画舫却始终没有动静,今夜艳绝半城的戏子唱腔中已经带了一丝哭腔。
旁人都以为他是入了戏,随了那戏中女子新嫁的悲喜,却不知他为自己而泣,恐惧包裹身体的那一刻,仿佛将血肉都冻成了冰,再随着动作一寸寸扭碎了。
最后两句戏文,哀怨缠绵,令人听之心碎,望之心醉,一双秋水般泠泠的双眸,闪烁着粼粼水光,似是将满月潭装进了眼里,落得一池星光。
等他唱完了这两句,后面就有小厮去请出钱最多的恩客。
往年最红的角儿,初夜拍了八千两白银。
已经有人设下了赌局,赌他温清淮能否打破这个记录。
可是……打破了又有何用呢?似那个坤角儿一般,从此当了人的姨太太?
龙阳本就是小众,往年如花似玉的坤角儿都只拍了八千两,一个男人又怎么配呢?
又不能生孩子,在外边养个娈宠不是一样的?
温清淮攒那攒,攒了许久,戏班子的那些女孩儿,得了钱就出去卖钗环首饰胭脂,男孩儿便要锦袍玉钗。
只有他,攒着自己的赎身钱,这么些年,唱成了第一名角儿,攒下来一万两银,只等着自己能为自己做主一回。
若是……若不是他,此身也只好永葬冰河……
早知如此,方才在后台就应该硬上了他!好歹也尝过一回那人的滋味了。
温清淮想到这里,恨恨地磨了磨牙,若是回到后台里,就是今儿折在这儿也定要尝尝那勾的人浑身犯软的玉茎是个什么蚀骨销魂滋味。
最后一个字拖的很长,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温清淮僵在那台上,好似一具没有生命的木偶人。
他最后望了一眼那紧闭的帘幕,咬了咬牙,眼角滚珠一般落下泪来。
泪滴到地上,他便要如一只凤凰一般折损在这冰水里。
死也要死的体面。
帘幕没有开起,只有悠悠一小船从那画舫地下缓缓驶出来。
在锁阳城,官方的金银兑换比例是一比二十,因为金子不是货币,往往铸造成的金元宝金首饰都不止这个价位。
金矿脉都掌握在城主府,连金店也都要城主府的批示才能得到黄金。
所以市面上的黄金价贵。
当然,白银也不便宜,比较普通老百姓都用的是铜钱。
梅云深敢公开把自己的竞拍价格砸到台上去,他就有这个资本碾压掉在场所有人的竞拍额。
三千两黄金。
按官方兑换比例是六万两白银。
别说是拍下这一个戏子,就是把春影班买下来当自己的私人戏班子都使得。
三千两黄金可不是闹着玩的。
整整三十盘金锭子,装在雕龙画凤的红木箱子里,摆在台上。
就为了竞拍一个戏子?疯了吧?这是有钱烧的慌?有这钱能买多少男孩女孩,一天睡一个睡到死都睡不完。
梅云深的价码并不只于这三千两黄金,还有十万两白银,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现成成的一箱子一箱子堆在台上,雕梁画栋的戏台,被这金银堆满。
盛装的戏子立在戏台子中央,被这金银衬得恍若人间富贵花。
真是疯了,这些金银打十个镶金的银像都使得,换来这么个身份下贱的玩意儿。
图什么?
有人觉得不值得,有人为金银痛心,也有人感概,原来戏本子里的情节是真的。
真的有这样祸国殃民的人物。
真的有一掷千金的高官豪客。
梅云深买的不止是他的初夜,也是他的身契。
原本春影班还有些犹豫,然后梅云深派人送去了一把宝刀。
要么把宝刀留下人送来。
要么把宝刀退回来,人还是梅大人的。
和和气气解决大家都体面,不能和气解决,也只能动用特权了。
“爷,您看这……”
小桃红端着放宝刀的托盘,层层帷幔
后,露出青色的衣角,修长的手指端着玉杯轻抿一口,唇角带笑。
“把人送去吧,他也是好命,遇到这么个不把钱当钱的主儿。”
玉杯磕在桌上,那修长的手指拇指上戴着浓绿的翡翠扳指,衬得那手指更加骨节分明,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手,更有一种苍翠的凌厉。
虎口和手指上带着薄茧,纵使保养得宜,也掩盖不住那呼之欲出的战斗力。
那手勾了勾,小桃红奉上宝刀。
帷幔后的人轻抚那嵌满了宝石带着异域特色的宝刀,毫不掩饰的赏识和爱惜,轻笑了一声。
“呵,你说他是不是打听过爷善使刀啊?不然送来的东西怎么如此合爷的心意呢?”
小桃红:……
爷!人家这是威胁恐吓啊!
“把那十万两白银送回去吧,这把宝刀可不止十万两,那个唱戏的也不值十万两。”
一个小玩意儿罢了。
“至于黄金,你去,去工坊里找个人给打成鸟笼子,爷想养只漂亮的鹰。”
三千两黄金,将近两百斤,得打个多大的鸟笼子?
属实是有那个大病!
“爷,这么多……”
“能打多大就打多大,爷的鹰可要住的舒舒服服的!你以为养雀儿呢?”
妈的,小桃红整个人都eo了。
今天遇到两个人,一个人挥金如土,一个人金笼养鸟,这都是什么人啊?
这世道,人不如鸟。
哦不,只有温清淮比得上面前这大爷养的鸟。
三千两金换一夜,十万两银换一人。
这唱绝了锁阳城的人间富贵花,到底是被人堆金撒银地连根带走了。
眼看着温清淮上了那画舫,众人只看绝色花落人家,却没看到那角儿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滑落的泪。
夜已深,别院里,温清淮身上的戏服嫁衣一般红的耀眼。
院中红梅盛放,房中暗香浮动。
今夜不知有多少人睡不着觉了。
在别院里陆文和陈玉宣都有自己的院子,两个人都失眠了。
陆文穴里是师父亲手塞进去的玉柱,狐狸尾巴从后穴里伸到外头。
他倒算是聊以慰藉,另外一个房间里的陈玉宣则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